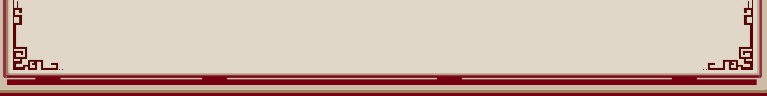|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刘愫贞

[原创2007-10-1707:01:27] The Modern Value of Legal Culture in the Language of Chinese Historical Judgment
The College of News Transmission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Liu Suzhen 内容摘要:中国历代判词语言折射出的传统法文化精神,具有很强的现代价值。中国历代判词语言传达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的伦理精神。这种法文化精神现在依然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礼法文化(包括以礼代律、以礼补律、以礼断狱)的现代价值,恶(Wù)讼文化的现代价值,重证据的(此处是否应有“现代”)价值和判词语言审美化的现代价值等,都具有学习借鉴的作用。 关键词:判词语言;现代价值;礼法;恶讼;审美化;证据
Summary Th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spirit reflected by language in historical judgment which interpret the essential spirit ----Confucianism spiri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is valuable in modern society and,influencing the whole society and lives of everyone constantly.It is significant to study the modern value of culture of conventions---including the replacement of legislation by conventions,the aids of laws with conventions,and the judgment of cases by conventions;malicious prosecution;evidence-emphasized phenomena;aesthetic language of judgment etc..
Key Words:language of verdict;modern value;the conventions of Confucianism;malicious prosecution;aesthetic language of judgment;evidence
法律文化是个复合的整体,而其核心就是价值体系。中国历代判词语言折射出的传统法文化精神,具有很强的现代价值。
中国文化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伦理文化。这种伦理文化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道德化、伦理化,于是“‘礼法合一’成了中国古代立法追求的最高成就。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华法系’实际是一种伦理法。正如张晋藩先生所说:‘……出礼入法,使法律道德化,法由止恶而劝善;以礼附法,使道德法律化,出礼而入刑。凡此种种,都说明了礼法互补可以推动国家及其有效地运转,是中国古代法律最主要的传统,也是中华法系最鲜明的特征’”。[1]这个最显著的特点,也透过判词语言折射在各个时期的判词中。中国历代判词又是中华法律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法律文化的具体表现。因此,透过中国历代判词语言所负载的法文化精神,揭示其基本特征,透视其现代价值,对建设民主与法制的和谐社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们虽然才思愚钝,但我们愿意努力去做。
我们这里所说的“法文化”,即学者们所谓的“法律文化”,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以“法文化”通称之。关于法文化的概念,一如“文化”,也是有多种不同的说法,这在刘作翔先生的《法律文化论》和马作武先生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等专著中,都有很翔实的介绍,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我们赞成这样的说法:“所谓‘法律文化’,包括法律意识与法律制度两个方面。法律意识又包括法律心理、法律思想学说等内容,法律心理是指对法律现象的一种直观的、感性的认识;法律思想是指对法律现象的系统的、理性的认识。法律制度包括法律规范(如法典、规章)、法律设施(如立法、司法机构)等等”,“在法律文化中,法律意识是深层结构,法律制度是其表层结构。法律意识尤其使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思想通常对法律制度起主导作用,它往往决定了法律制度的特色和样态”[2]。中国历代判词是传统法文化的司法表征。
中国历代判词语言传达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一直贯穿于中国社会,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规范着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心理。这种法文化精神现在依然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我们这里想探讨的的是判词语言所折射的法文化精神的现代价值。
(一)礼法文化的现代价值
我国古代以礼治国,礼法合一。“礼”最初只不过是“一切祭祀活动”[3]的统称。“礼”本字为“禮”,从示从豐,“礼是一种祭器,示是一种仪式”(费孝通)。后来,随着国家的出现,“礼”的职能就逐渐转变为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最高原则,“成为早期国家划分社会成员尊卑贵贱地位及其相应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依据”[4]。《礼记·曲礼》明确地告知了这一点:“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不庄。“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仲尼燕居》)。这段经典名言,先连用八个“非礼不”的句式,说明“礼”在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无所不在性,后又用两个比喻句,论证“礼”在社会治理中的不可或缺性。对“礼”的这种普遍性作用,梁治平先生是这样概括的,他说:礼“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人作道德评判和法律裁判的最后依据,也是渗透到所有制度中的一贯精神”[5]。“礼”在成为社会普遍适用的规范和调整各种关系的准则的同时,就自然具有了“法”的意义。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礼法文化形成的轨迹。在周代刑法是包含在周礼之中的。就连当时的司法官——司寇的设置,也是在《周礼》中规制的:“惟王治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6]。由于礼与法的关系极为紧密,以至于有些学者就认为,周代是无刑罚的“礼”的天下,美国著名法学家昂格尔就认定“礼是主导性的并且是几乎唯一的正当行为的标准”。汉代礼与法几乎一体,形成“礼为体,法为用,失礼则入于法。‘礼者,民之防,刑者,礼之表,二者相须犹口与舌”[7]。这种一体化在《唐律疏议》中被凝练为两句名言:“德礼为政教治本,刑法为政教之用”,尊“礼”为文教德化之根本,降律“法”为治国安民之工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介绍说:“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采用之,元时断狱亦每引为据。明洪武初,命儒臣同刑官进讲唐律。后命刘惟谦等详定明律,其篇目一准于唐。”董建辉先生认为,后代的法律仅在一些具体条文上作过不大的变化,对于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核心“以刑弼教”、“修刑以复礼”的宗旨却恪守不渝,“礼”所涵盖的家庭、伦理与社会的等级差序成为法典的基本内容。他说:“入宋以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致力于把原来属于士大夫以上阶层专有的‘礼’进一步社会化、大众化,使之成为所有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以至于到明清时期,礼法制度和礼法精神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传统中国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8]。
这一法文化精神贯穿于中国历代判词的始终,准确地说,从西周的钟鼎文判词、汉朝董仲舒的“春秋决狱”直到清代的判词,无不张扬着“礼政为主,刑政为辅”的礼法文化的精神,司法官们尽力把法与刑伦理化、礼法化。概而言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判词其一,以礼代律。《明公书判清明集》中的《检校嫠幼财产》判,就不大符合宋朝法律。依照宋朝法律,此类事件本不在检校之列,只是因为方天禄之“妻方十八而孀居,未必能守志”,司法官即以权变法,对方天禄的财产实行检校。在这道关于财产检校问题的判词中,财产归属尚在其次,是否“绝支”的宗嗣问题倒是根本问题,简校的出发点和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财产,而是在于昭示宗法伦理原则,至于法条的规定则随“礼义”而变通:“妻在者,本不待检校,但事有经权,十八孀妇,既无固志,加以王思诚从旁垂涎,不检校不可”[9]。清朝名吏樊增祥在《批郝克栋呈词》一判中,因为郝克栋逼讨郝氏兄弟已故的授业老师所欠钱款,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于是,他便随意地将这欠款充作了郝氏兄弟的谢师礼金,这就将此项借贷法律关系归于消灭,债权人的权益没有受到保护,而是维护了封建的礼教道德。樊增祥在《批开阳县贡生李铭灌呈词》的判词里,公然打出“天伦为重,财产为轻”的礼义道德大旗断案,这是一道因管辖不合而不准的判词。判词是这样的:“弟兄析箸,即有不平,可凭亲族处理。处理不公,可向县官局控。即使县断不公,为君子者,当以天伦为重,财产为轻,岂有控省恳提,害人而兼自害之理”[10]。如果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服制、亲属关系时,为了维护伦理道德原则,可以不顾法律的规定,以礼断案。例如,清人李钧的《判语存录》中收有“郑元臣与其甥郝南枝斗殴纠纷案”的判词,其内容梗概是这样:舅舅郑元臣控告外甥郝南枝之妻陈氏,气死了自己的妹妹、南枝的母亲郑氏,南枝又殴打了自己。李钧在判词中辨疑析理,以礼说案。他指出,郑元臣诬告其甥郝南枝,其“情重,应合反坐”,诬告反坐是封建法律的一条基本原则。可是根据本案的具体案情,却不能适用这条法规,因为“平情而论,郑氏虽不死于气,而陈氏失于提防,则咎无可逭也。元臣虽非伤于殴,而南枝敢于冒犯,则罪无可辞也”,因此,判郑元臣不予反坐;判词对郑元臣借南枝十五千和盗卖南枝家骡子所得的十六千,“均免追逐”,这就将郑元臣的全部债务判归消灭,最离奇的决断是:郑元臣盗卖郝南枝家的骡子所得价款归属盗卖者郑元臣所有,此判处与法律规定大相背离。但是裁判结果之所以能够成立,就是因为原告与被告双方是甥舅名分的关系,为了“以全戚谊”[11],置法律规定于不顾,以伦理原则做依据决狱断案,以维护封建的宗法制度。这种以礼决狱的做法,因受到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推崇,而大行其道。
其二,以礼补律,礼律并用。在历代判词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有些案件中,当法律规定不够明确或者没有明文规定时,司法官们常常以礼义补充法律,加强了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效果,有力地维护了封建宗法秩序。《清朝名吏判牍选》中,收有张船山关于王小山顶凶卖命“案件的判词,是这个观点的有力支撑。被告屈培秋因“口角细故”,用刀杀人,并使王小山顶凶卖命。这样以来,屈培秋便是“以一案而杀二命”,判词认为,“屈培秋以口角细故,用刀杀人,其罪已不逭,而又不束身司败,以二百金买人一命,藐视王法,殆无是过。夫使二百金可买一命,则家有百万可以屠尽全县。以一案而杀二命,其罪更何可恕!须知,前一杀尚出于一时愤恨,或非居心杀人。后一杀则纯为恃富杀人,有心杀人。误杀者,可免抵;故杀者,不可免也。屈培秋应处斩立决,并于行刑前,先仗二百”,对杀人凶手,依照法律规定,严惩不贷;王小山顶凶卖命,依照大清律例,应该处以仗责之罚,王桂林“贪图二百金之微利,至将亲爱之子,付诸刀俎之下,不特犯国法,且无人情,依律应处无故杀害子女罪减等,仗二百,流五千里”[12]。然而,判词却对父子二人“一体准予免责”。这个判决,与大清律之规定,不合而有悖。但是这个判决之所以成立,是因为王小山的行为,完全出自一片’孝心,为养活父母计”,又因为王小山在受审时,明确表示了“愿以一命牺牲,不累堂上”的至孝之心,因此,对其父王桂林也不予责罚。这个判决使用孝治原则代替法律规定,补充律例,律礼并用。这样的例证在历代判词中,虽不能说比比皆是,却可以随手拈来。
其三,以礼断狱,宽缓刑罚
在历代判词中,用忠孝伦理原则判案断狱的判词,在一程度上,起了宽缓刑罚的作用,定很好地体现了封建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提倡尊尊亲亲的孝义行为。《孝经》有“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的说法,历代统治者也号称以“孝”治天下。这在历代判词中得到了很好地贯彻。例如清朝名吏樊增祥就有这样的判例。他任渭南县令时,遇到一个命案:村民李虎娃因为佃农彭某与自己的母亲通奸,而杀死了彭某。在法庭上,李虎娃“‘到县侃侃自承,谓向与彭同炕而宿,肇衅之夕,彭与同鸡奸,愤不可遏,故以刀毙之,愿论抵’。由于樊增祥对十八岁的李虎娃狂斫杀死粗硕如牛的彭某,觉有不类,遂反复开导,最终究出了实情。樊增祥于是拟详免除李虎娃之罪,详文中有‘李虎娃弱龄杀奸,挺身认罪,其始激于义愤,不愧丈夫;其后曲全母名,可称孝子’语,被认为是‘折狱警句’”[13]。一个剥夺了他人生命的人,因其杀人的动机出于“孝义”,所以,就可以免除惩处。这种宽缓刑罚的做法,在客观上还是有利于老百姓的,也可以看作是封建法制文明进步的一个方面。
在这种以礼代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礼”的违犯的惩处是通过刑罚的手段实现的;同时,“礼”具有法的统摄作用,使之其在法典的制定、法律的实事、案件的讼诉、量刑的依据等方面,都浸淫着封建的等级差序和纲常伦理,因而,“礼”势必成为判词中决狱断案的依据。
礼法文化有它的负面价值,也有它的正面价值:注重道德教化,提倡和谐的人伦秩序,在处理民事法律关系时,常常有法规律条不能替代的作用。在执法过程中,恰当地使用一些礼义道德的教化,不仅有益于个案的解决,更有益于推动社会法治化的有效运转。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转变矛盾的对立、斗争的思维方式,而要从协调、平衡、共处的统一性视角去观察和处理问题,并以此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在这个理论基础的指导下,在处理决断一些案件尤其是民事案件时,用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规则,化纠纷于和解,融矛盾于协调,对于社会的和谐、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都有益而无害。
(二)恶(wù)讼文化的现代价值
我国的恶(wù)讼文化认为“词讼息结,极为美事”,厌恶诉讼,以无讼为有德。无讼是中国历代社会追求的理想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孔孟之流从人性中发掘出礼义之道;法家从人性中找到的是‘以刑去刑’;荀子儒法兼容,从人性中导出礼义和法度,从而为传统中国追求实现无讼的基本模式的形成指明了方向”[14]。这就是说,古人追求的理想社会,其根本形态是无讼的,“争讼乃是绝对无益之事,政府的职责,以及法律的使命不是协调纷争,而是要彻底地消灭争端。为做到这一点,刑罚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教化”[15]。整个一部《明公书判清明集》的司法功能,就是抑制诉讼,追求无讼。恶(wù)讼的法文化,同我国古代以农耕自然经济为社会经济的主体相适应,或者说,它是这种农耕自然经济在法律上的一种反映。在狭小封闭的经济生活模式中,仁义伦常是社会规范的手段和教化的工具,若有纷争,人们也多采用道德礼义的教化,使之忍让谦和、息事宁人。老百姓们也以“打官司”为不光彩的事情,尽可能不去涉讼。中国历代判词所体现出的这种法文化精神,主要表现在:
一是法官们视那些或无理取闹、或曲意诬告的具讼者为“刁民”、“顽民”,对他们极尽喝斥、责骂之能事,如在清朝名吏樊增祥的判词里,就经常出现“糊涂已极”、“两造混账之尤”、“如此横蠢”、“世间糊涂混帐,如尔夫妇者,可谓至极而无以复加”等;于成龙关于江峰青与申宗氏双方小孩殴击一案的判词里,用“若妄思争讼,饬词干渎,本县先将尔拘县惩办”,严厉警告原告,以免他再涉讼。樊增祥在《委审临潼民人房秀柱上控房太明一案详稿》中就有“讯明后,重加刑责,以夺健讼之气”的话,是因为在证人证据以及法庭查验后,断定原告房秀柱“屡次诬牵”“自十八年兴讼,施、傅两令,念其年老,未加刑责”,结果他不但不思悔过,反而“上控官长,任我所为”,认为官长“始终不责一板”,于是便“何所畏惧”的一次又一次的诬告、具讼,严重干扰衙门公务。因此他认为对于这类民人,必须予以严加管束,惩一儆百,以便整肃诉讼秩序,维护固有的封建礼法等级关系。
一是体现在判词中法官们对所谓“小事”不予受理、且流露出的厌恶态度,如樊增祥《批章忠孝呈词》[16]中就有“左臂铁尖伤一点,不过米大也,值得打官司乎?尔真不是东西”;樊增祥在《批陶致邦呈词》这样批示:“胡说八道,尔之妻女不听尔言,反要本县唤案开导,若人人效尤,本县每日不胜其烦矣。不准”[17]。什么为“小事”,在封建立法与司法中并无明确的界定,其“大”与“小”之别,全由司法官个人权衡估量,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百姓们的诉讼要求和法律意识,在客观上形成了恶讼、息讼的社会风气。即使产生了纷争,人们首先运用的是忍让、调解等非诉讼手段。
一是司法官认为证据不足不予受理的诉讼。这可用樊增祥的两道判词为例。其一为《批张星焕呈词》,其不受理的理由是:“据称尔鳏居求耦,石廷璧窥尔薄有蓄积,诡媒赚骗等语。尔既出钱娶妇,自应打听确实,何竟听其一面之词,倾囊相付?自春至秋,屡称该妇病重阻婚,尔亦可以悟矣。乃犹将石廷璧殷勤款待,奉之如祖神明。直至七月以后,廷璧之妻吐露真言,尔始恍然大悟。不但绝无其事,抑且并无其人,世间讨老婆心切,如尔之发昏者,盖亦鲜矣。其痴呆也可笑,其被骗也可怜。惟交钱既乏中人,议婚别无媒妁。词内要证,惟廷璧之妻一人。试问夫为被告,妻为中证,岂肯背夫向尔?是尔不但妻房无着,银子乌有,并且官司也打不成。本县实代为着急之至。此秉不准,另秉候夺”[18]。其二,在《批抱告王升秉词》中,也是因为“捉贼未见脏”,即证据不足,而没有受理:“尔主在店失物,即请追店主;若在衙署失物,必请追东家矣!语云:捉贼见脏。究竟你的师爷曾否看见店家偷窃否?著明白禀复,此秉不准”[19]。
在民事纠纷事件的解决中,历来国人都是以“息”讼、调解为最佳方法,双方当事人“对簿公堂”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解决之法。调节的方式不限一种,有官方的,更有民间的,包括乡保、族长的调解。明律就曾规定:“各州县设立申明亭,凡民间应有词状,许耆老里长准受理于本亭剖理”(《大明律集解附例·刑律·杂犯》)。在清代,尽管法律明文规定,民事纠纷应该有乡保查明呈报,“该州县官务即亲加剖断”(《大清律·刑律·诉讼》)。但是,大量的民事纠纷却是在民间调解处置的。梁启超的《中国文化史》中,就记述了民间调处的通行性,他说:
每有纷争,最初由亲友耆老和解,不服则诉诸各房分祠,不服则诉诸叠绳堂。叠绳堂为一乡最高法庭,不服则诉于官矣。然不服叠绳堂[20]之判决而兴讼,乡人认为不道德,故行者极希。子弟犯法,如聚赌斗殴之类,小者上祠堂申诉,大者在神龛前跪领鞭扑,再大者停胙一季,或一年,更大者革胙。故革胙为极重之刑罚。耕祠堂之由而拖欠租税者停胙,完纳后即复胙。犯盗窃罪者缚其人游行全乡,群而共噪辱之,名曰“游刑”。凡曾经游刑者,最少停胙一年。有奸淫案发生,则取全乡人所豢之豕行刺杀,,将豕肉分配于全乡人,而犯罪之家偿豕价,名曰“倒猪”。凡曾犯倒猪罪者,,永远革胙。
这种恶(wù)讼的法文化价值取向,其正面意义在于:一方面,这种追求政治生活稳定、人际关系和谐、社会运转有序的目标,有利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和对矛盾的冷静处置,这种和谐的社会关系,也正是法律的目标;另一方面,也可以阻止一些恶意诉讼,避免其带来的危害——损害诉讼相对人的合法利益、浪费国家司法资源、扰乱正常司法秩序、冲击司法权威和诉讼价值等。但是其负面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中国百姓守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凡事以忍为上”,“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信条,轻易不愿进入法律程序,这就使得一些应该使用法律手段解决的纠纷矛盾,或者被“私了”,或者矛盾被激化,这些行为都严重地阻碍、减缓着社会民主法制化的进程,妨害着社会和谐的构建。我们必须冲破“恶(wù)讼”的传统法文化的桎梏,注重培养百姓运用法律程序,来解决争讼的法治理念。这种理念的培养,应从制度与精神两个层面,通过渐进方式来实现,以达到用程序和规则解决社会上的不和谐问题,构建和谐社会。这也正是恶(wù)讼文化的反面价值。
(三)重证据的法文化现代价值
从历代判词反映出,司法官们比较重视有关证据。宋人宋慈编著的《洗冤集录》一书,“总结了传统法医学的经验,为司法实践中查证和认定事实,提供了法医学根据,成为司法活动中具有指导作用的理论著述。为了保证法医学检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的客观性,保证法医学方法的可靠性,从宋代起,我国封建法律规定了较为系统的律例内容,规范法医学方法的应用……在证据学方面,宋代同样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例如,关于证据方法,郑克在其《折狱龟鉴》中曾作过较为全面地论述,他指出;:‘鞠情之术,有正有谲,正以核之,谲以挞之。术苟精焉,情必得实,恃拷者乃无术也。’这里‘正’即‘或以物证其慝,或以事核其奸’”[21],强调使用证据的作用。据高珣先生统计,在《明公书判清明集》中,司法官们使用过的证据主要有五种:其一为书证、包括契约、账簿、书信及图册等;其二为物证;其三为证人证言;其四为检验结论——主要是各种文书的鉴定报告;其五为勘验笔录——主要为有司人员的现场勘验结果报告。例如《折狱新语.》卷一中的《冤命事》判词中,就有“初汝能犹执石女之说为诬,及召两稳婆验之,信然”[22],明确地交待了证据和证明的方法,并确认了查证事实。清代判词亦用各种证据,判案断狱。张船山的《陶丁氏拒奸杀人案》的判词中,有现场勘验结果报告、对死者伤势的检验报告以及“各方推勘”的结果等证据,使对杀人者陶丁氏判处无罪的结果,可靠可信,铁案如山。前文所述因证据不足而不受理的判词,也能证明古代司法官们重证据的一个方面。唐代著名判词专集张桌(?)的《龙筋凤髓判》卷一有道判词,说御史严宣,弹劾长史田顺受脏二百贯。因严宣曾被田顺鞭打过,严宣会不会是“挟私弹事”?经过“勘问”调查,判词认为“贪残有核,脏状非虚。此乃为国锄凶,岂是挟私弹事?二百镪坐,法有常科;三千狱条,刑兹罔赦”[23]。判词说明了弹劾行为成立的实质要件是证据。只要是证据确凿,(“贪残有核”),就不是“挟私弹事”,就是“为国锄凶”。判词还认为御史弹事,无论所弹对象是什么人,只要证据确实,弹劾行为就能成立,就是正确的。把证据看作行为成立与否的实质要件。樊增祥《批岐山县徐令秉》是一道“为施行审判职能”的判词,根据案件的证据,他认定此案的性质为“既无人命,又无奸情”,不支持岐山县令的“请将全案提省,交谳局彻底根究”的处理意见,要求其立即释放所有人证。这既是他严肃执法的精神所在,更是他重证据的的司法理念的体现。
重证据的法文化价值,对今天法制现代化建设、对司法的公正客观,都有借鉴作用。尽管我们现在的司法与执法活动,都有异常强烈地重证据精神,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个别司法与执法活动中,仍有证据不实的现象存在,佘祥林案件,决不是仅此一例。因此,我们依然还得认真地继承并学习古代重证据的法文化精神。
(四)判词语言审美化的现代价值
历代判词的语言审美价值很高,尤其是宋代、明代与清代的判词语言。汪世荣博士认为:审视明、请的判词,可以判定“中国古代判词已确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地位,这主要表现在:首先,从表述看,判词字斟句酌,遣词用句极为严格,而且继承了唐代判词重文学色彩的表达方式,具有很强的欣赏价值”[24]。下面我们以宋明清三代的判词为例,论述判词语言审美化的现代价值。
第一,质朴凝重而生动有情。《明公书判清明集》的大部分判词语言都呈现这一特点,例如:卷之十,方秋崖所拟判词《祖母生不养死不葬反诬诉族人》,全文照录如下:
阿王生而孤老,所当供养者其子孙也;死而葬埋,所当经理者其子孙也。子孙零落,独有一胡师琇尚存,乃飘弃出家不顾。祖母生则族人养之,死则族人葬之,为师琇者,尚何面目立天地之间哉!族人裒金而葬,以其不利也而迁焉,与其他发掘塜墓,不可同年而同语也。使当职处此,迁葬者本自无罪可科。今所司既为将两人勘锢,监迁原处,为师琇者亦可已矣。至经上台,嚣讼不休,然则养其祖母,葬其祖母者,乃师琇之雠人耶?不可谓知恩报恩者矣!此盖贩卖丘中之骨未满其意,亲死之谓何,又因以为货,不孝者也。在法,供养有缺者,徒二年。此师琇祖母在时之刑也。骨肉相弃,死亡不躬亲葬敛者,于徒二年上重行决配,此师琇祖母死时之刑也。罪在十恶之地,从轻勘仗一百,编管邻州,申照会[25]。
这道判词,凝重雅朴,虽篇幅不长,但事理周详,合礼合情又合法。作者先运用了两个排偶句:“生而孤老……死而葬埋……”,指出供养和葬埋阿王的事情,理所当然地应该由她的子孙们承担,生养死葬,乃后人对老辈的义务和责任,不可推卸、无可逃避。这是中国社会人人应遵守的指导性道德法则,更是儒家的伦理规则。两句句末的两个语助词“也”,显示了作者劝谕世人的谆谆之情。下面作者先用一个对句“生则族人养之,死则族人葬之”,说明了阿王是由族人养生葬死的,她唯一的后人胡师琇并未尽半点责任。于是作者便反问道:“为师琇者,尚何面目立天地之间哉!”这是第一次对胡的谴责;族人曾因“其不利”而迁了阿王之墓,现在已令“迁原处”,胡师琇就没必要再兴讼了,作者用“为师琇者亦可已矣”一句,告诉胡师琇:应该知足了,你并没有什么资格和理由,来讼告你的族人,这是第二次谴责;如果说这两次谴责,作者的心情还算平静的话,那么,紧接着的一个长句子,就不那么冷静那么和颜悦色了:你来到堂上对养你祖母、葬你祖母的族人,“嚣讼不休,然则养其祖母,葬其祖母者,乃师琇之雠人耶”,这些人难道不是你的恩人反倒成了你的仇人吗!作者情愤不已,这是对胡师琇的第三次谴责,也是最动感情的一次,因为该人是个不遵守儒家伦理道德,既不知尽孝又不知恩报的顽愚之徒,已经到了难以理喻的地步。对这种“骨肉相弃,死亡不躬亲葬敛”的不孝子孙,应依法从重惩处,因其“罪在十恶之地”。在这里,与其说是依法严惩胡师琇,倒不如说是据礼严惩来得更确切:因为胡师琇首先违背了伦理纲常,其次,背离了“无讼为美”的宗法制原则,从法律的角度他并没有需要重处的违法行为;用词用语平实质朴,却极具感****彩。又如,《明公书判清明集》卷之十,胡石壁所拟《兄弟侵夺之争教之以和睦》判词和卷之八翁浩堂所拟《衣冠之后卖子于非类归宗后责房长收养》的判词。胡的判词较长,我们只引开头一段文字,即可窥全豹:
大凡宗族之间,最要和睦,自古及今,未有宗族和睦而不兴,未有乖争而不败。盖叔伯兄弟,皆是祖先子孙,血气骨脉,自呼一源。若是伯叔兄弟自想欺凌,自相争斗,则是一身血气骨脉自相攻相克。一身血气骨脉既是自相攻相克,则疾通病患,中外交作,其死可立而待矣。故圣人教人,皆以睦族为第一事,盖以此也[26]。
翁浩堂判词全文如下:
父子,人伦之大,父老而子不能事,则其罪在子;子幼而父不能养,则其责在父。刘珵为衡州知郡孙,有男元老,幼不抚养而卖与乡民郑七,弃衣冠而服田亩,情亦可怜,此犹可诿也,曰刘珵一时为贫之故。已而元老不安于郑七家,逃归本父,刘珵固宜复回天理,自子其子矣。乃复以元老卖与程十乙,则其意安在哉?可谓败人伦,灭天理之已甚者!今郑七入词,欲取回元老于已去三年后,此决无复合之理。元老宦裔,郑七农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应更来识认。刘珵两将元老卖弄,为父不父,本合勘仗,且与丛荫,决小仗二十。元老碟押往族长刘万二宣教宅,听从收养。观此子情貌硷狡,兼所习已乖,请二万宣教严钤束,庶免堕落下流,为衣冠之玷,亦一美事[27]
胡判的开头旨在告诫诉讼当事人,兄弟之间亲情大于财利,骨脉重于争夺,这种“亲亲尊尊”的伦理原则,是圣人赖以教化的“第一事”,万万不可违背。否则,“傥或因一朝之念,兴阋墙之争,兄则欲害其弟,弟则欲害其兄,以贼害之心,内施于手足之间,则异于禽兽者几希矣”。作者谆谆之诲,拳拳之情,溢于言表;语言运用平易无奇,字里行间情切意深。翁判是一道典型的维护封建等级宗法制度的判词,他认为“元老宦裔,郑七农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能将元老再归还给养父郑七,以免为官宦之“玷”。他把“父父子子”的伦理原则摆在文首,然后高屋建瓴地述说等级的不能逾越,“为父不父”的“灭天理”“败人伦”的行为之可憎。强调等级观点,虽是错误的,但语言运用却值得称道,通俗质朴,寓雅致于平实之中,比如“父老而子不能事,则其罪在子;子幼而父不能养,则其责在父“两个对句,平常词语,两种情况,一个道理,述说得既透彻又确切得当。在述说刘珵第二次把自己儿子卖掉时,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懑之情,指斥这种行为是“败人伦,灭天理之已甚者”。这两道判词的语言风格,都呈现出语言质而有文,拙而优雅,语气恳切,说理深刻而富有感情,语言凝重而不乏勃勃生气的特点。
第二,词浅意明、典雅雍容而又切合法意
明代判词的语言风貌既承宋代判词语言的“散”特征,又较之宋代判词更多地使用典故,其语言不仅词语浅切典雅雍容,而且还处处切合法意,不因典故的运用而丝毫降低判词的司法功能。如,李清《折狱新语》卷一《冤命事》判词[28],这是一道离婚纠纷案的判词,全文录下:
审得汪三才去妇大奴,陈汝能义妹也。先因三才父继先,曾出银廿两,聘大奴为三才妇。夫大奴一石女耳,此固夭桃摽梅之无感,而蜂媒蝶采所不过而问焉者也。及同衾后,三才悔恨无及,即将大奴送还汝能讫。非敢奢望于蓝田之生玉,正恐绝望于石田之生苗耳。则汝能之返其聘金也,宜矣。何迁延不偿,且以冤命控乎?初汝能犹执石女之说为诬,及召两稳婆验之,信然。无论阳台之云雨,其下无梯,正恐井不孕石耳。然则为汝能者,将令三才于飞之愿,仅托巫山一梦,而不复为嗣续之绳绳计乎?是面欺也。应仗治汝能,仍追聘金廿两,以结此案。
这是一道典型的散判判词,整道判词只使用了一组对句:“非感奢望于蓝田之生玉,正恐绝望于石田之生苗”,这两句中含有两个典故:“蓝田生玉”出自《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恪少有才名,孙权谓其父瑾曰:‘蓝田生玉,真不虚也’”。这里是指三才根本没指望大奴为自己生一个有大出息的儿子;“石天生苗”出自《左传·哀公十一年》:“得志于齐,犹获石田也”,这里用“石田”喻指大奴是个不能生育的石女。散体判词并不排斥典故,这道判词还使用了好几个,如“照井而生”引自《后汉书·沃沮传》:“或传其国有神井,窥之辄生子云”(“其国”指传说中的女儿国),说明大奴根本无生育能力;又如“于飞”,反用《诗经·大雅·卷阿》“凤凰于飞”之句,指明三才与大奴夫妻不可能和谐生活;再如,引用《诗经·周南·螽斯》:“宜尔子孙,绳绳矣”一句,点出汝能所说,是饰词捏控的当面欺诈的行为。所用各典,贴切自然,紧紧围绕着判案的需要,不离题不臆断。语言典雅雍容,而又浅切意明。
《折狱新语》中的判词,还采用文学创作的一些基本方法,不仅对事件作生动的具象描述,而且整个判词富有隐喻色彩:对于某些事实,难以进行直接的叙说,作者也无权随意杜撰,只能借助于想象的手段和富有抒****彩的议论,突出事件本质、深化法理,在情与理的相互生发中,决狱理案。例如,卷一的《强占事》[29]判词,即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审得柳士升妹三女之许嫁刘有义,乃故父一龙命也。迨迁至今,则有义家徒四壁,仅可咏骤富于新月耳,然一诺千金,著于皎日,何必聘金也?胡为士升者,乃于母董氏合谋,以三女另许,不过俞永鼎之十六两,动其新涎耳。初阅永鼎诉辞,谓“成婚二载,亦既抱子”。信斯言也,无论深红尽落于狂风,而有子离离,已垂嫩绿。当以三女为鸦头女,而返之不祥耳!及当堂提质,则十三室女也。青青一枝,犹未“灼灼其华”,而遽云桃花贪结子可乎?诞哉!兹召三女面讯,则与有义母张氏执手相依,情若母女。而问以适刘乎?适俞乎?曰:“适刘,虽母兄不能强也。”夫女子之嫁,母命之。“人尽夫也”,是何言与!“逼迫有阿母”,犹坚弗承;肯云“理实如兄言”?噫!我知之矣。“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女所惭,不可告婿也;聊以而执姑手明心尔。若此愿不遂,则投烈火以明烈,而赴清流以矢清,皆可因言而定志者也。合断还有义,返耳东床。仍仗治士升、永鼎,以为贪财、渔色之戒。
这道判词依然是关于婚姻纠纷的案件。柳士升之妹柳三女,许嫁刘有义,是其父生前的命令,可是士升与其母却贪财让三女另嫁。但三女矢志非刘有义不嫁,法庭支持了三女的主张,惩罚了有关当事者。作者在整个判案过程中,生动形象的叙写与富有法理意味的抒情相生相长,把一道司法判词制作成一篇极具文学色彩的美文。对刘有义家贫的说明,先用一句实写:“家徒四壁”,语义很明,一般文案都是如此表示;可李清却还要化用黄山谷的诗句,对有义家贫来一个形象地叙描:“仅可咏骤富于新月”,带有解嘲意思。写到三女许嫁刘有义时,先有“一诺千金”之句,又接一句“著于皎日”。此句出自《诗·王风·大车》:“谓予不信,有如皎日”。为古人发誓明心迹之词,用在这里,形象地告诫士升等人,三女当年的订婚,是指日为证、重于千金、不能更改的。“无论深红尽落于狂风,而有子离离,已垂嫩绿”,隐喻如像俞永鼎所言,三女现在已成为生子养孩的妇人了;“青青一枝,犹未‘灼灼其华’,比喻三女年小还是个未成人,这就犹如桃树,花儿尚未开放怎么可能就结桃子呢;“投烈火以明烈火,而赴清流以矢清”喻指三女非刘有义不嫁的决心。在这些隐喻般的手法之中,作者又适时地抒发感慨,仅单纯的感叹词就有:“诞哉!”;“噫!”等使其前面的叙述说理,更有情采。
这类判词,较之宋代更具文学色彩,比之唐代判词更通达流畅。但《折狱新语》过多地引经据典,影响语言的质朴与通晓,也是后世判词不大取法的。
第三,爽畅老辣,典雅有容
这是清代判词语言的一个显著特点。清代判词语言不藻饰华美,“不雕饰,不假借,不著色相,不落言诠”,一般不借助其它表现手法和修辞手段。但却尽显或“清水出芙蓉”,或“豪华落尽见真醇”的美质,这也是语言运用的高境界。樊增祥的大部分判词、海瑞《胡胜荣人命案参语》、张船山《拒奸杀人之妙批》、陆稼书《乡董不法之妙批》等判词,都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下面我们以张船山的《陶丁氏拒奸杀人之妙批》判词为例,试作以说明。其判词全文如下:
审得陶丁氏戮死陶文凤一案,确系因抗拒****,情急自救,遂致出此。又验得陶文凤赤身露体,死于丁氏床上,衣服乱堆床侧,袜未脱,双鞋又并不齐整,搁在床前脚踏板上。身中三刃:一刃在左肩部,一刃在右臂上,一刃在胸,委系伤重毙命。本县细加检验,左肩上一刃最为猛烈,当系丁氏情急自卫时,第一刃砍下者,故刀痕深而斜。右臂一刃,当系陶文凤初刃后,思夺刀还砍,不料刀未夺下,又被一刃,故刀痕斜而浅。胸部一刃,想系文凤臂上被刃后,无力撑持,即行倒下,丁氏恐彼复起,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猛力在胸部横戳一下,故刀痕深而正。又相验凶器,为一劈柴作刀,正与刀痕相符。而此作刀,为死者文凤之物。床前台上,又有银锭两只。各方推勘:委系陶文凤乘其弟文麟外出时,思奸占其媳丁氏,又恐丁氏不从,故一手握银锭两只,以为利诤;一手持凶刀一把,以为威胁。其持刀入房之时,志在奸不在杀也。丁氏见持凶器,知难幸免,因设计以诱之。待其刀已离手,安然登榻,遂出其不意,急忙下床,夺刀即砍,此证诸死者伤情及生者供词,均不谬者也。按律因奸杀死门载:妇女遭强暴杀死人者,仗五十,准听钱赎。如凶器为男子者免仗。本案凶器,既为死者陶文凤持之入内,为助成****之用,则丁氏于此千钧一发之际,夺刀将文凤杀死,正合律文所载,应免予仗责。且也强暴横来,智全贞操,夺刀还杀,勇气加人。不为利诱,不为威胁。苟非毅力坚强,何能出此!方敬之不暇,何有于仗!此则又敢布诸彤管载在方册者也。此判[30]。
上面所引判词出自《清朝名吏判牍选·张船山判牍》,是一道无罪判决文书。判词前的事实部分为:“陶文凤者,涎弟妇丁氏美貌,屡调戏之,未得间。一日其弟文麟因事赴亲串家,夜不能返。文凤以时不可失,机不可逸,一手执刀,一手持银锭两只,从窗中跳入丁氏房中,要求非礼。丁氏初不允,继见执刀在手,因佯许也。双双解衣,丁氏并先登榻以诱之。文凤喜不自禁,以刀置床下,而亦登榻也。不料丁氏眼快手捷,见彼置刀登榻即疾趋床下,拔刀而起。文凤猝不意,竟被斩死。次日鸣于官,县不能决,呈控至府。张船山悉心研审,尽得其实。即下笔判陶丁氏无罪”。这段文字,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判词,不特起一个背景的作用,更能衬托出判词语言运用的佳妙之处,故录于此。张船山认定被告丁氏是无罪的,不仅无罪,还应该“布诸彤管载在方册”,传之于后世,供人学习,以表彰她在“强暴横来”之时,能“智全贞操”的行为。我国传统文化非常看重妇女的贞操,无论是妇女自己,还是整个社会都把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判词认定被告丁氏不受金钱诱惑,不畏强暴威胁,靠智慧保全了自己的贞操,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值得大加表彰的。因为她的行为既符合法律的规定,更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因此,作者才敬而褒之。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里他称赞的是“贞操”,而不是她的生命。在张船山们看来,贞操重于生命,若丁氏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是应该的、天经地义的。
从语言运用的角度审视这道判词,极大张扬了爽畅老辣、典雅有容、精于用词、工于炼句的风格,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
这道判词语言的爽畅老辣、典雅有致,首先表现在对死者身中三刀的叙述。先总说三刀的位置:“一刃在左肩部,一刃在右臂上,一刃在胸”,接着用一句话“委系伤重毙命”,点名被害者的死因。然后用“本县细加检验”一句,承上启下,连续铺排了三个因果句,用“故”字一顿,异常清楚地把前因和后果展现出来,因,是事实,果,是推论,有理有据,言明理足,叙述眉目极为清晰,语言运用极为简洁,干净利落,无一赘字。整段文字没有用瑰丽的词藻进行修饰,也不用重彩繁笔做工细描画,写原因,仅用简约洁净的笔触作以勾勒,实事实情直笔书写,对胸部一刀的述说,尤为精当,“想系”、“即行”、“恐彼复起”、“索性”“再”、“一不做二不休”等词语,,把死者的动作、丁氏的心理活动以及丁氏砍最后这一刀的力量大小等情景,都毕现于读者眼前。爽畅无华,确切难移,作者把词语锤炼到了这一极高的境界,纯净的词语似平白却极典雅,在质朴中隐现着无尽的峭拔老辣。
这道判词在裁判部分,尤显出其语言“爽畅老辣,文雅不俗”的特点。在大量的散句中,作者一口气排出了六个四字句:“强暴横来,智全贞操,夺刀还杀,勇气加人,不为利诱,不为威协”,寓对称于参差之中,藏感情于议论之内,互为关联的意思,用四字句出之,在高低起伏的节奏中,充溢着作者无比的敬佩赞叹之情。在张船山他们看来,丁氏保全的不单是她的“贞操”,更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因此,一种敬佩之情便油然而生,使得他禁不住要一唱三叹,话语表现层层递进,情感抒发由浅入深。先用四字句叙事议论,蕴含赞叹之情;接着,从人的意志角度,使用一个假设句,赞美丁氏具有非常坚强的毅力;下面作者诚惶诚恐地表示,敬佩尚且不及,那里还敢仗责呢?行文至此,作者内蕴的感情直泻而出,充满了无比的喜悦之情和赞美之意。
张船山的这道判词,给人一种明快刚健、清越骏发的美感。李涂在《文章精义》中说:“文章不难于巧,而难于拙;不难于曲,而难于直;不难于细,而难于粗;不难于华丽,而难于质”。“巧与拙”、“曲与直”、“细与粗”,基本上是指写作技巧方面的问题,而唯独“华丽与质”是专指语言的问题。张船山的判词,却能弃易而就难,选择质朴而摒弃华丽,并能写出了上乘的判词,留给我们悦人心志的美文,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驾驭语言功力之深之厚。当然,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必须附丽于它的内容,否则,就成为文字游戏。从这道判词,我们可以看出,张船山对律例案情了如指掌,谂熟于心,再加上他的语言能力,就有了这“辞愈朴而文愈高”的判词。
我们认为判词语言的审美化,具有很强的现代价值。司法文书的语言,要通俗但不能词语贫乏言不及义,要朴质但更要血肉丰满富有文采。任何体裁的文章,都需要美感,都需要吸引人的魅力,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制作者遣词造句的能力。认真学习古代优秀判词的语言运用方式,汲取其中的语言运用营养,对我们现代司法文书制作质量,有百益而无一害,在这方面,陕甘宁边区的一些司法文书堪称楷模。
(刊载于《美中法律评论》2007年第7期;在该刊扉页上的“本期导读”中,(介绍了四篇文章,本文为第一篇)这样介绍:“中国历代判词语折射出的传统法文化精神,具有很强的现代价值。刘愫贞在《中国历代判词语言的法文化价值》一文中指出,中国历代判词语言传达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的伦理精神。这种法文化精神现在依然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礼法文化(包括以礼代律、以礼补律、以礼断狱)的现代价值,恶讼文化的现代价值,重证据的现代价值和判词语言审美化的现代价值等,都具有学习借鉴的作用”)。
--------------------------------------------------------------------------------
﹡此文系“中国法学会法学科研2003年度科研项目”(会研字[2003]3号)《中国历代判词语言的法文化精神及其价值的现代透视》的子论题之一。
刘愫贞,女,西北政法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陕西省语言学会会长、中国法律语言学术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应用语言、法律语言与法文化。
通讯地址:西安市长安南路300号:西北政法大学107#信箱,邮编:710063
电话:029-85385084Email:muer166@sohu.com
[1]崔永东《中西法律文化比较·序》,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2]同上,第4页。
[3]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礼》,中华书局1959年版。
[4]马作武《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5]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14页。
[6]董建辉《“礼治”与传统农村社会秩序》,《新华文摘》2005年第19期。
[7]同2。
[8]同上。
[9]《明公书判清明集》(上),第280页。
[10]汪世荣《中国历代判词研究》,第102页。
[11]《中国历代判词研究》第208-209页。
[12]《中国历代判词研究》,第200-201页。
[13]《折狱龟鉴》卷八,转引自汪世荣《中国历代判词研究》,第228页。
[14]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5]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7年版,第217页。
[16]《新编樊山批公判牍精华·批牍》卷十。
[17]同上,卷三。
[18]汪世荣《中国历代判词研究》第104页。
[19]同上。汪世荣博士认为,司法官不予受理的判词,还有管辖不合不准的批词、原告无实体权力不准的批词、原告无权利不准的批词、书状不合不准的批词等,不过,这几类不受理的判词,均不属我们所讨论的恶(wù)讼范畴,自不涉及。
[20]叠绳堂,乃梁氏宗祠。
[21]《中国历代判词研究》,第35页。
[22]李清《折狱新语》卷一,第8页。
[23]《中国历代判词研究》,第40页。
[24]《中国历代判词研究》第36页。
[25]《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第386页。
[26]《明公书判清明集》(下),第369页。
[27]同上(上),第277页。
[28]李清原著、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注释《折狱新语注释》,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29]《折狱新语》,第69-70页。
[30]《中国历代判词研究》第110-111页。
来源:一位法律语言学教授的博客
(西北政法大学法律语言研究中心发布)
|